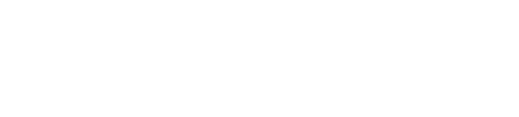啤酒知识 


早些时候,英国考古学家和中世纪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朗兰兹出版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精酿啤酒:传统工艺的起源和真正意义的探究》。这本书的目的是重新找回“手工艺”的含义,因为它在成为营销口号或精品店出售的昂贵商品之前就已存在。朗兰兹以学者的眼光回顾过去,挖掘这个词的原始含义,看看它如何丰富我们当前的制造方法,在一个有机器或应用程序为我们做事的世界里。
我不想引发任何争论,但这是事实:工艺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越来越难以准确地表述一个足以满足每个人的定义。当然,这与制作有关,而且制作具有可感知的真实性:手工,充满爱;来自原始的天然材料;达到所需的标准。但它并不一定会产生一个对象。最近对精酿啤酒的热潮意味着我们可以消费精酿啤酒,但实际上却一无所获。在艺术世界中,它既可以是一种方法论过程,也可以是一种概念工具。在奢侈品的世界里,一种保证是你正在获得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产品……但即使在今天“工艺”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中,它与“工艺”的定义也只有最微弱的重叠。一千多年前它第一次出现在书面英语中时就已经出现了。
朗兰兹从语言学、经验和哲学角度进行探索,翻转这个主题,考虑它的历史和与语言的联系、物理步骤以及与大师的交谈。他还参与制作过程。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介绍不同类型的传统工艺,例如盖屋顶。朗兰兹使用他的所有三种研究模式来考虑茅草(他告诉我们这个词来自古英语þæc,屋顶,但得出的结论是这并没有多少智慧),并让读者对一个简单的物体有比他们更深刻的理解。曾经想象过。
这本书从朗兰兹第一次偶然涉足手工艺开始,当时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一把旧镰刀。一位路过的司机告诉他如何正确使用它,出于好奇,他整个夏天都继续使用它。当镰刀不再是概念性的时候,他学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花园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直线被宽阔的曲线所取代,角落变得圆润。” 这种非概念性的洞察力使他对“工艺”的古代含义以及现代人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克雷夫特意味着什么
Cræft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词,朗兰兹研究了它的使用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含义是在知识、能力和一种学习的背景下的技能的力量。此外,一种心理技能的感觉——优点、天赋或卓越——出现的次数与身体技能感。” 后来,他总结了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
“手、眼、头、心、身的协调让我们对世界的物质性有了有意义的理解。”
这个概念在中世纪并没有被描述或定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前工业时代,一切都是手工制品。这个术语几乎以负空间的形式存在,只有当我们能够在机器上批量生产东西时,它才有意义。然后,了解人类如何手工制作东西以及当我们将它们交给机器时会丢失什么就变得很有价值。
对于朗兰兹来说,技艺是存在于身体中的知识。当我们重复做一件事时,我们就会开始掌握;我们的身体经过一千次重复之后,知道如何做一件事。这就是Cræft的中心点:智慧和技能来自工匠的身心,而不是机器。他必须在这里做一些拆包工作。人类非常聪明,我们制造机器已有数千年历史。其中一些使工艺变得更容易,但不会妨碍身体的智慧(例如围绕重物移动的机器);其他人则这样做。他用一个最英国的例子解释了这句话的重要性:
修剪树篱的工艺可以分为三个物理功能。第一是权力的运用。第二个是动觉敏感性,它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身体、手臂和手塑造成一个位置,从而使我们能够实现第三个,即切割的动作……我不认为使用电动绿篱机的修剪师是真正的工匠的理由很简单,即该工具削弱了与他们正在工作的实体的材料属性的接触程度。
工具和机器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偶然的,工具让工匠能够运用力量和“动觉敏感性”,而机器则消除了这些能力和“动觉敏感性”,而这正是工艺的本质。
精酿啤酒
当然,我读这本书有一个特定的议程:我想知道朗兰兹的观点如何帮助我理解工业啤酒和精酿啤酒之间的区别——如果有的话。(除了我上面引用的提及之外,他在书中没有考虑啤酒。)这曾经看起来如此明显,但我们越仔细研究它,我们就越会被无关的考虑所困惑。

啤酒并不是最容易考虑的工艺,因为它几乎从一开始就利用了机器。它是一门复合工艺,从田间到杯子,要经过多次操作,而不是像用镰刀割干草那样简单。一路上,使用各种工具和机器来移动重型原料,操纵和组合它们。对工艺的规定性定义只会让我们陷入定义允许的做法的泥潭。如果不使用机器,就不可能以商业规模生产啤酒。问题是:这些机器什么时候才能将工艺从酿造中移除?
工艺存在于工匠的身体和智慧中,而不是机器中。一些设备实际上为啤酒酿造商投入了更多的能量——例如,漩涡使啤酒酿造商能够向啤酒中注入一定剂量的啤酒花。但每次啤酒厂将部分流程自动化时,它都会将啤酒制造商手中的智慧转移到机器中。机器精确且一致地做事,但每次我们用它们代替物理行为时,我们就离流程越来越远。这些小让步的增加使酿造行为从主要由啤酒厂定义转变为由啤酒厂定义。智慧从人转移到机器。
我采访了数百家啤酒厂,其中许多人是在参观他们的啤酒厂时采访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磨练了自己的技艺数年或数十年。他们已经生产了数千批啤酒。更资深的酿酒师——John Keelings(Fuller's)、Hans-Peter Drexlers(Schneider)和 Jean Van Roys(Cantillon)——所传达的东西不仅仅是深厚的经验。他们暗示着他们对啤酒的了解,但他们并不总是能表达出来;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当您与曾在自动化程度不高的啤酒厂工作过的经验丰富的酿酒师交谈时,您会听到他们暗示“工艺”。
他们经常诉诸类比、隐喻或诗意的语言,而这正是最好的啤酒写作的素材。然而,总有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我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与酿酒师 Adam Brož 一起参观布德瓦尔啤酒厂。即使对于捷克共和国来说,布德瓦啤酒也是一种不寻常的啤酒。一次又一次,我们会讨论啤酒厂的一个特质,布罗兹就会求助于科学。该啤酒厂做了很多研究,他用研究来证实他们的方法。如果我轻轻地指出发现不同结果的研究,他会微笑;他认识他们所有人。但布德瓦尔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的做法,以及布罗兹学到的、现在正在实践的做法,对他来说有着直观的意义。这些过程和啤酒是密不可分的;在布罗兹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中,他都能感受到啤酒的效果。工艺品。
我将用朗兰兹的另一段话以及关于它如何应用于啤酒的评论来结束这篇很长的文章。他观察到:
在艺术世界中,自由美可能会因对功能的依赖而受到污染:形式和外观应始终被视为纯粹美学的一部分。但我会判断一个好的钩子的锻造,不是看它的美观程度,而是看它的形状与我用过的其他钩子的形状有多接近。它的吸引力——以及它的美丽——取决于它作为钩子的功能。我们越来越与依赖美作斗争,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放置或使用功能性的工艺品。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来衡量这种美丽。它依赖什么?我们对温暖毯子的真正价值感到挣扎,因为我们的中央供暖系统永远不允许我们变得足够冷。
啤酒不像钩子或毯子那样是一种功能性商品。然而,在每种类型的啤酒中都蕴藏着巨大的人性财富——我们的农业资源、我们的喜好、我们的饮酒方式、我们的历史、战争和饥荒留下的伤痕、法律的残余,以及酿酒师为之奋斗的所有方式。几代人都根据这些现实调整了他们的工艺。当一位工匠大师(酿酒师)在她熟悉的啤酒厂酿造第一千次或第一万次啤酒时,智慧就会传承下去。当同一位酿酒师决定将这种智慧——不仅是在酿造过程中,还有人们如何消费和享受她的作品的知识——投入到一种新啤酒中时,这种智慧、这种工艺就会得到发扬光大。
在另一个极端,高度工业化的过程看起来与此相反。新啤酒的灵感不是来自酿酒商,而是来自营销团队。它的轮廓是由从酿造行为(某些风味或市场利基)中去除的抽象概念定义的。这种啤酒被设计为在只能以有限的方式酿造啤酒的机器上酿造——新啤酒必须遵循机器的限制。啤酒的参数被输入计算机,新口味的啤酒从另一端出现,无需参考一长串的人工输入。这显然不是什么技巧。
大多数啤酒厂位于连续体的这两点之间。使用工艺逻辑,很容易想象,一家公司拥有的大型啤酒厂比一家缺乏经验的家庭酿酒师经营的小啤酒厂更接近真正的工艺。但在每种情况下,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啤酒厂,而不是规模、所有权结构或其他常见指标。我总是对最新的发明或趋势感兴趣,但我真正喜欢的啤酒不仅仅是聪明的产物。但酿酒大师的产品,充满了更深层次的工艺智慧,通常更令人满意。也许我可以写一篇关于我们如何 更具体地使用这个概念来思考啤酒的文章,但现在就足够了。